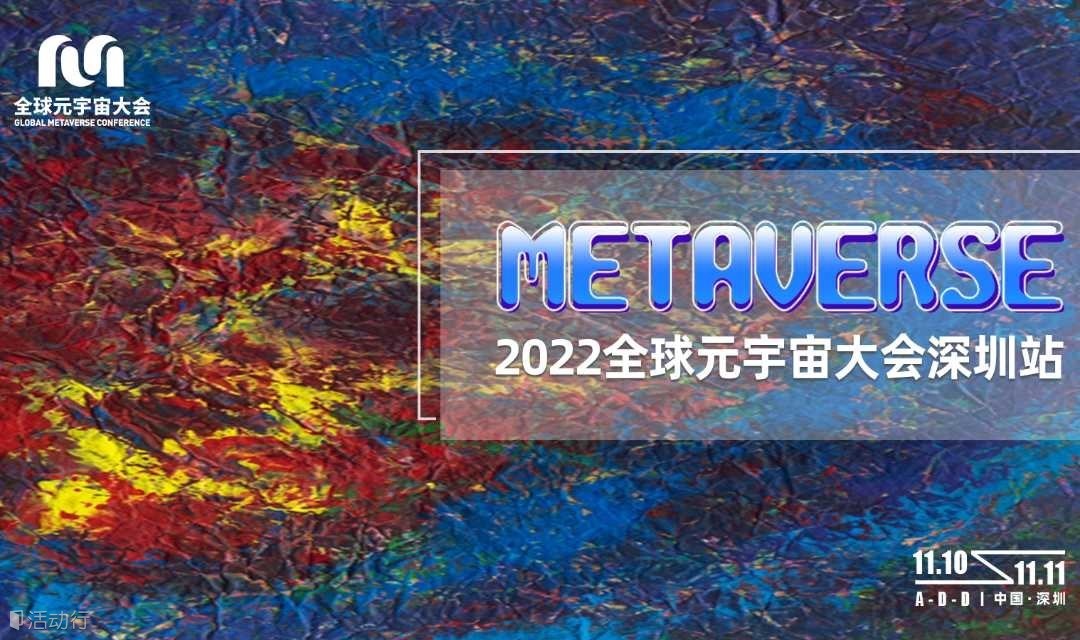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TOP创新区研究院(ID:TOP_Lab),头图:Pixabay。
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我们从资本时代逐渐转换到知本时代,从“管理型”经济彻底转向了“企业家”经济,从制造驱动变成了科技驱动,从以生产有形商品为中心转变为以创新和知识为中心。
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的竞争不能只看存量,更要看创新的能力。
创新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一套系统。
我们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可以看做是“跟随策略”的成功,某项技术已经成熟,且在市场得到成功验证,确定性很强,各方敢于下注。
但随着改革进入到深水区,发展接近荒茫的无人区,前面的路就特别要强调“创新引领”。
创新的道路是一条高度不确定的道路:技术路线可能出错,初创公司可能失败。传统的自上而下管理战略在跟随期好用,在创新期可能就是掣肘。
这时,最好的方式就是培养环境,培养环境的关键在于设计创新这个游戏的规则,即创新制度。
美国构建成功创新生态的一个秘密就是“双长制”。
所谓“双长制”,就是由一位经验丰富的CEO和一位拥有尖端科技的教授(首席科学家)合作,形成创业企业的核心。
有趣的是,一般来说首席科学家在公司里是兼职,他的主要工作还是在高校里做研究。
“双长制”现象的背后其实也是制度设计的结果。创新核心在于鼓励创新的制度,如果没有产生鼓励创新的制度,单纯靠技术实验室、大学研究所,是很难走向持续创新的过程的。
Moderna,“双长制”的典型案例
Moderna大家都不陌生,它与辉瑞BioNTech合作,用了不到12个月的时间共同研发了首批针对COVID-19的mRNA疫苗,在快公司去年发布的全球最具创新力公司的榜单中排在第一位。
公司的核心科技是mRNA技术,它的用处不仅仅是疫苗开发,当我们有能力掌握mRNA的秘密后,可以用mRNA来合成任意一种想要的蛋白,并对人体进行潜在的治疗,可以应用在癌症、慢性病、疫苗等众多领域。
更让人惊讶的是——这只是一个1200人的生物技术公司 —— 完全称不上“大公司”,但公司的市值已高达600亿美元左右。
Stéphane Bancel自2011年开始在Moderna当CEO,是哈佛商学院的MBA,管理经验非常丰富。
在Moderna之前是法国诊断公司bioMérieux SA 的CEO,之前在礼来(Eli Lilly)多年,担任过比利时董事总经理以及全球制造战略和供应链执行董事的职责,礼来之前,是bioMérieux的亚太区市场总监。
Moderna的首席科学家是Robert Langer,这可是位大神级人物。
Langer教授是美国国家工程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据估计是“历史上最多产的医学发明家之一”,获得了世界上最大的发明奖 Lemelson-MIT 奖;“历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医学工程师”,他在 Google Scholar 上的引用次数超过 32万次,发表的文章超过 1500 篇。
不过,人家的主要工作是在MIT当教授,是MIT的12 位学院教授之一(学院教授,Institute Professors,是教授可以被授予的最高荣誉),大部分时间是跟学生们待在用自己姓氏命名的Langer实验室搞研究搞发明。
而,Moderna只是Robert Langer教授知识变现的其中一个公司,此人还有多家公司,而且他发明的专利已被许可或分许可给 400 多家制药、化学、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
作为Moderna的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Robert Langer占有3%的股份,轻松跻身“3逗号俱乐部”(身价超10亿美元)。
另外,联合创始人Noubar Afeyan博士也是一个相当能打的“六边形战士”:有非常多的身份,学者、企业家、投资人、在众多领域游刃有余,经验值拉满,战斗力五格,真·全方位无死角。
普遍的“双长制”
是不是只有初创公司如此呢?不是。像谷歌这样的巨无霸也是如此。
产业易逝,创新永存。
想要站在时代的浪潮之巅,就要有敢于进取、颠覆自己的勇气。
Google通过搜索引擎这个赚钱机器,几乎垄断了利润,但未来呢?新的Google在哪里?所以,Google的创始人们始终保持危机感,他们改名字叫Alphabet字母表,希望通过培育尖端技术,收购科技公司,覆盖机器人、通讯、智能医疗等从A到Z的所有产品与服务。
Alphabet这个大系统中,有很多正在研发的、处于萌芽状态、模糊状态的颠覆性技术,但都不是在原有的组织体系里实现的,是在“创新中心”、“X实验室”,“臭鼬工厂”中实现的,比如waymo就是Google X孵化的产物。
这些创新研发中心是如何取得成果的呢?仅仅靠招人吗?远远不够。
创新需要的成本越来越高,需要的创新人才越来越多;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聪明人都在你手下工作”。
所以,Alphabet会主动与学界建立伙伴关系。
它每年投资超过250项科研项目,在例如arXiv的公用数据库和自有研究站点发布研究成果,每年邀请约30位正在休假的顶尖学者来Alphabet的创新研发中心一起工作。
创新中心则会为科学家们提供独有的研究环境、无可比拟的数据集、世界顶尖的运算架构以及不断公开出版的机会。这些学者在体验过之后,大多数都愿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继续跟Alphabet合作。
几乎所有世界级的技术公司,都在全球开设了各式各样的创新研发中心。
比如华为,它不仅有自己的研发中心,也与业界10余个运营商共同建立了28个联合创新中心,成功合作的重要创新课题超过100个以上。在这些联合创新中心中,很大一部分合作对象就是高校。SingleRAN、IP微波、融合计费平台都是联合创新中心做出来的成果。
如果华为对某一个领域感兴趣,它会追踪这一个领域所有的学术研发组,通过合作的形式进行“预研发”,最大限度地增加创新的概率。
为什么是双长制?
制度。创新需要激励,不管大家怎么看重情怀,但最重要的激励方式之一就是金钱回报。
1970年代左右,美国国内经济萎靡,在外深陷越战泥沼,国内滞涨严重,在商业上受到了来自日本的激烈竞争。
为了应对诸多挑战,美国国家队开始入场,利用国家的力量资助高科技初创企业的发展。同时制定了一个革命性的法案——《 Bayh-Dole Act 贝多法案》。
在贝多法案之前,教授在学校拿的是政府的经费,做出来的研究发明也是归属于政府。教授可以用专利出去开公司,但政府也可以授权给第三方使用专利,如果这个第三方是个已经有资本有渠道的大公司,你出来做公司基本就是死翘翘,没有任何竞争力。
这并不公平。
所以美国的大学联合起来向民主党参议员伯奇·贝赫(Birch Bayh)与共和党参议员鲍勃∙多尔(Robert “Bob” Dole)抱怨,两位议员提起了《Bayh-Dole Act 》,核心是将以政府财政资金资助为主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发明者所在的研究机构和发明者本人,并且让研究机构和发明人可以独享专利的经济利益。
事实证明,贝多法案对于后来美国的产业升级、以及美国科研的知识技术产业化有重大的影响。
首先,科学家创业者开始出现,这些大学里的研究者用政府的经费搞研究发明,因为可以享受到专利的经济利益,不少大学教授还纷纷出来办公司,成为了万亿级的富豪。这在贝多法案之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其次,博士毕业生们更愿意当留在大学当教授了,因为不仅可以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自己也可以从中获益,名利双收,源源不断地输出最前沿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成功创业后,有些成为连续创业家,部分则转化成为天使投资人,支持新的科技创业者,形成了“科学家—创业者—天使投资人—新的科学家”的“人才循环”模式。
现在,大家都在打“创新”牌,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不少公司所谓的创新只是“商业模式创新”而已。
不过,模式创新再复杂,红利时代已经过去,“低垂的果实”已经所剩无几,创新需要向深科技迈进,进入到新型材料、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区块链、无人机和机器人、光子学和电子学以及量子计算等领域。
这些领域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才能有所作为,于是有实力有技术的专业人士(know-how)才能够真正有竞争优势,获得资金和其他关键资源。
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让有know-how的人更愿意成为创业者?如何从制度上保证他们的利益?如何让创新生态有长久的后劲?
科研创新、产业竞争本质上就如同生物演化,进步都是随机试错的结果,充满偶然性。通过制度设计,在足够的基数条件下,就可以把偶然变成必然。
本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创新湾(ID:EnnoBay)立场。如有异议,请与我们联系。创新湾聚焦新科技、新产业领域,致力于记录中国科创力量,让更多人洞见未来。(报道、转载、进群,联系微信:EnnoBay2020)


扫码进群



.jpg)